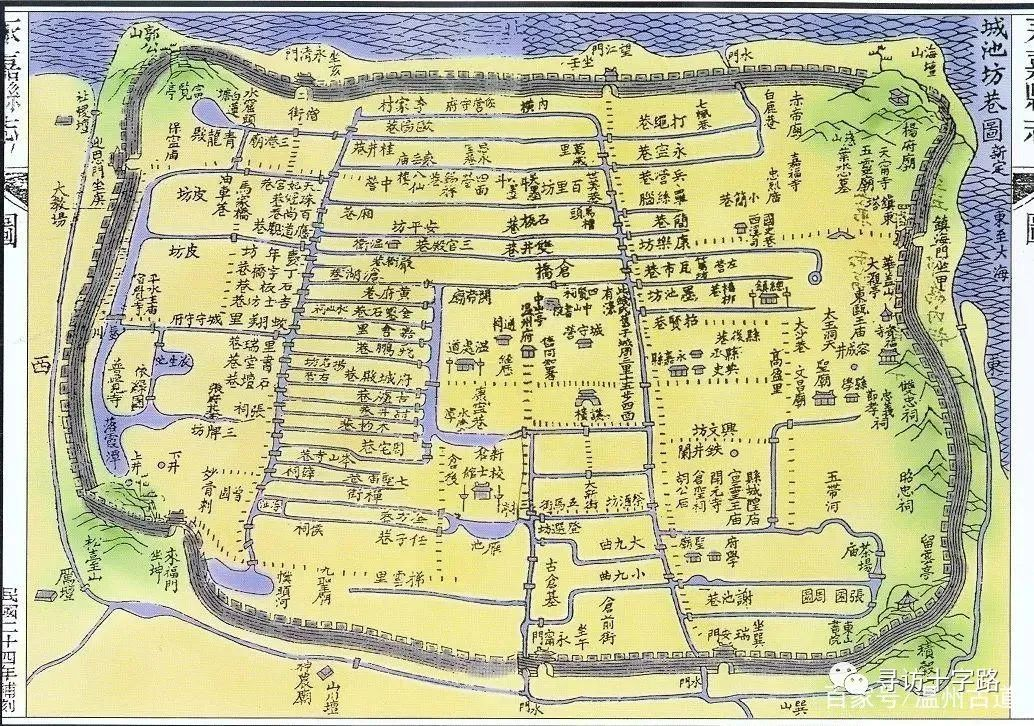2023年经历了许多事件,也寻访考查了不少地区古代和近代的宗教遗址,原本的计划是2023年走完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城市,但因中途发生了意外,计划只好搁浅。在调养了半年之后,笔者还是毅然决然的去了一趟福建泉州,结束了2023年的最后一次宗教历史考查。
回到寄居的城市不久,又备着打包,返一趟老家过春节,这一年的时间就此匆匆而过。回首2023,真是“几多风雨,几多沧桑”。刚回到故乡,当地几位教会历史工作者随及登门喝茶坐谈,并呈上刚出炉的“成果”--当地教会史一册,心中倍觉欣慰,感恩!
交谈中,笔者突然想到,今年正是基督教内地会在离家不远的岐头山建休养所130周年。于是,在第二天除夕夜晚上约了教会历史工作者谢弟兄,决定大年初一去探究内地会在岐头山休养所的遗迹。
图:内地会岐头山休养所,也叫避暑屋,俗称“番人馆”。
(载自《亿万华民》1903年版,第69页)
一、关于“番人馆”和始建
岐头山内地会休养所,也叫避暑屋、度假屋,当地人俗称“番人馆”,据外文资料标注的英文,“番人馆”有一个积极向上的美好名字,译为“盼望之屋”或“希望之屋”,若用当今时髦的话命名,应该叫“希望别筑”。关于岐头山内地会休养所背后的故事,以及当时为何要在瓯江口的岐头山建造这样一座供宣教士疗养、避暑的房屋?笔者通过和教会历史研究工作者座谈交流,同时查阅了宣教士所留下的相关资料,对岐头山“番人馆”的历史有了大概的了解。
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自1854 年入华,1865年6月27日正式创立中国内地会以来,就特别注重各地区县市(包括农村)的福音工作,一批又一批宣教士投身中华各地,在不同的领域发光作盐,成为当时中国老百姓的祝福。无论是在教育、医疗,还是在戒毒等方面,内地会都是各宣教差会传播福音的皎皎者。1866年,内地会宣教士曹雅直从上海转至宁波,一年后,曹雅直在蔡文才陪同下到达温州。而当时的沿海地区因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,当地人对黄头发蓝眼睛的“番人”,充满着排斥和敌意,因此,内地会的宣教士每天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,同时福音事工的进展也困难重重,加上日常生活更是异常辛苦!
图:1891年中國內地會宣教士合影
后来进入的内地会宣教士,同样面临布道环境的艰难,以及生活上营养缺乏等方面的问题,时间一长,导致身体出现了一系列毛病。同时,他们时常又遭遇当地一些瘟疫和流行病的传染,种种困难,都让晚清入温的一些宣教士在体力上出现了超负荷。据资料显示,晚清温州地区的人们平均寿命不超过30岁,很多宣教士更是英年早逝,平均寿命不超过35岁[1]。1879年,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,因事工劳累,在山东烟台休养调理,为了更好的开展今后的事工,戴德生准备在当地购地建房。两年后,属内地会总部的芝罘学校和疗养院建成。
1893年春,身在温州的曹明道师母(温州福音拓荒者曹雅直太太薛氏)因福音事工忙碌,缺乏休息,导致身体严重透支。四月的一天,在晨祷中突然休克,经过医生的诊断,需要暂停工作,静心调理休养。由于本地一时没有好的居所环境,当时曹明道只好辗转到山东烟台芝罘内地会总部休养所进行调理。四个月后,当她回到温州后,看到宣教士照样面临环境和身体的问题,心中就有感动,希望上主带领!也能在温州建立一所供宣教士休养、避暑的场所,这个想法后来得到了内地会其他几位宣教士的响应[2]
图:山东烟台芝罘内地会疗养院
于是,在1893年的圣诞节,温处两地内地会几位宣教士经过集体商议,决定参考之前戴德生在烟台芝罘建立疗养院的模板作法,欲在温州地区选址建一所供宣教士休养、避暑的聚所,以方便长期在浙南地区传教的牧者的身体调整,今后更好的投入到各地的福音事工。
经过几个月的择地选址,和当地教友的推介联系,最后,终于购得瓯江口岐头山靠海边的一处山坡台地。这处位置环境极佳,南眺瓯江,北靠山梁,东西群山绵绵,帆影点点,可谓春暖夏凉。再看近有山脊左右环绕,使得休养所凸显的位置形成一块“半岛型”高台,伫立此地,清幽静怡,是疗养、避暑的绝佳之地。
据曹明道师母后来的回忆中谈到,对温州的第一印象,觉得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城市,特别进入当地的海岸线时,感觉自己回到了古老的苏格兰。这也许是她建造休养所,为何选址在岐头山的一个原因吧!
1894年,岐头山休养所开始动工,工程由曹明道师母主要负责,而在实际建造的过程中,因为休养所远离市区,距最近的岐头村也要翻过几座山岗,所以材料的运输是第一个要克服的困难。但就是在物资和人工匮乏,以及交通运输困难,经费不足的情况下,曹师母却亲自加入施工队伍,并和一起参与的同工边干活边为此祷告,同时安排主日聚会等,可以说,曹明道师母为此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。经历坚持不懈的大半年,休养所终于建成,吸引了山下附近的村民前来参观,后也时有参与礼拜,当地人称它为“番人馆”。
二、探寻考查“番人馆”的经过
说到岐头山“番人馆”,除了山下岐头村的一些长辈知晓外,当地其他人少有知道,温州及乐清的文史资料中也没有记载。只是在一百多年前宣教士的传记和资料中有所提及,特别在外文资料内地会会刊《亿万华民》上留有一张乐清岐头山休养所的照片,成了目前当地最早的几张老照片之一,也是拍摄“番人馆”的唯一照片。
十年前,当地教会历史工作者白云贵根据曹明道等著作留下的线索,和历史资料所刊登的“番人馆”照片,来岐头山进行了实地考查,终于使温州内地会休养所准确的位置被发现并证实。此后又引起当地一些教会历史工作者的重视,特别是研究内地会的历史学者。近年来,当地教会历史工作者开始大量走访,并采访到岐头村当年和“番人馆”宣教士有过交往的长辈后裔,听他讲述岐头山“番人馆”的前尘往事。2020年之后,当地教会历史工作者为了整理《乐清内地会》的资料,也曾多次来“番人馆”探寻。除此之外,几乎没有人来此寻访探究过。
笔者从史料和老照片中看到,这座以曹明道师母为首,负责建造的休养所,在当时,对于瓯江口往来的船只来说,绝对是非常显眼的建筑。而且它具有中式传统建筑及融合的特征,矗立在荒芜的山岗上,结合瓯江上的点点帆影,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。照片中的画面虽然有些模糊苍凉,但拍摄的角度和位置却是非常到位,完整诠释了天地物的亲和一体,使得照片中有山有水,有船有房,有田有路,这种画面合理的布局,展现了拍摄者高超的艺术技巧,以及对“番人馆”整体和周边环境的定格记录,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。
为了实际查考“番人馆”旧址的模样,大年初一的午后,笔者在谢弟兄的亲自引导下,驱车前往岐头山,一路穿越村庄,过黄华关,到了岐头村,这里是朱姓后裔的族居地,山脚下有明代进士南昱的墓。据县志所记,岐头山又名崎头山;它像一道天然屏障,雄踞在瓯江口北岸,同时紧邻温州四大古海关之一--黄华关。明清以来,这里一直都是军事要塞。
图:岐头村的老巷
我们继续驱车沿盘山公路而上,不一会儿,就到达一处山脊拐转位置,这里地势平整,南眺瓯江(古称慎江。七里港段,被孙中山在《建国方略》里称为“天然良港”),西南瓯江北口跨海大桥气势如虹,东面有明代岐头寨古烽台(当地人称“烟墩”[3],北面望山下河流纵横,沃野阡陌,楼宇林立。这处山脊上开辟了一块水泥地的平台,供岐头村和游人晨练之用。
图:谢弟兄在杂草密林中披荆斩棘开道
我们一行三人在丛林中来回的打转,不知不觉又回到原先的位置,谢弟兄又不停的搜寻,渐渐往下攀爬,来到一处水泥砌成的小屋旁,他说道:“上次就是从这小屋边经过,继续往下。”此时他心中似乎有了把握和方向,我俩随即也跟了上去。
图:好几座被草丛掩埋的“无名”坟墓
图:好几处都是挡道的枯枝断木
图:好多带刺的树木,查阅后得知叫“刺楸”,别名“刺桐”
一开始,从山脊平台往下爬,就一直没有一条像样的路,我们仨都是在杂草和密林中穿梭,想想如果换成独自来考查,再加上胆小的话,还真不敢探寻此地。自从谢弟兄断定了准确的方向后,我们心中一下子踏实了很多,也知道“番人馆”确实离我们不远了。只是还要在荒草、乱石、断树上翻越,笔者好几次手险些被刺划破,裤子摩擦着枯枝,鞋底沾满了泥,简直就是连滚带爬式地搜寻。
只记得爬越了两处倒地的断木,再往前稍左拐,一堵石头围墙映入眼帘。谢弟兄急忙说道:“到了,就是这儿了!”笔者一下子凑到前面,心中实在非常激动。苦苦寻找了老半天,终于到达了目的地--“番人馆”旧址。但眼前的景象和老照片对比,使笔者的心情一下子失落了许多,130年前的宣教士休养所,竟会是如今这般模样,一片荒凉,杂草覆盖。谢弟兄从东面墙基旁往上绕到遗址中心位置,而我呆在那里凝视着一块块石头垒砌的围墙墙基,近距离的观察墙基上方存留的几块青砖残片,又打量着东围墙周边的环境,以及当时休养所东边高台尽头的悬崖处,希望能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。
图:“番人馆”遗址北首屋后的位置
图:“番人馆”遗址前靠东悬崖陡壁
图:“番人馆”遗址东面围墙墙基
谢弟兄和同伴在上面的遗址平高台处召呼笔者上来,于是,笔者只好沿着一处非常陡峭而又坍塌的墙基往上爬!随行同伴站在上面赶忙拉了笔者一把,终于到了番人馆遗址的高台处,这里杂草茂密,已经很难辩证“番人馆”面积和布局,我们又从遗址中央位置往西,因为那边还有一段保存相对完整的围墙墙基。
围绕着“番人馆”,我们整体的查考了它的遗址现状,整个区域几乎全部被杂草覆盖,有的地方草已长到一米以上,因为有一段矮小的墙基延伸暴露,所以大概能分辨出四方屋子的形状,屋的位置地上所长出来的杂草,与其它地方有明显区别,但四周看上去非常杂乱,一片荒芜。遗址台的左边有三颗盘口粗大的树,出类拔萃,看似是周边最大的树木。站在树旁位置,能眺望到瓯江和遗址平台下的现代灯塔、马路,台子中间和靠右的前方完全被众多的杂草和断木挡住视野。过到右面的缘边,又是一堵围墙墙基高高耸立,并且保存非常完好,比左侧的围墙墙基保存的还要好,看上去很平整修长。站在围墙墙基上,能看到西南方的瓯江北口大桥非常雄伟壮观,遗址斜对西北方紧邻着一座现代佛教寺庙。虽然“番人馆”遗址全部淹没在杂草树木中,但整体的面积不大,呈半圆形,根据目测在二三百平米左右,东西长度约有13米,南北长度约有20米,背靠山梁,虽野径枯木丛生,但仍有清风习习之感。
图:“番人馆”遗址上的枯枝断木随处可见
图:“番人馆”遗址东南角的树木和眺望口
图:“番人馆”遗址前方正中间和西南方被树木杂草覆盖
对比当年传教士在岐头山所拍摄刊登在《亿万华民》上的照片,可以看到,130年前的“番人馆”孤零零地矗立在瓯江口的山岗上,除了这两栋比较明显的房屋,周围的环境和山头看上去光秃秃的,但东边的山坡上却有一片片山梯田,延伸到山下,远处的瓯江上点点帆影若隐若现,虚无缥缈。当年拍摄的角度是从东往西方向,拍摄者是站在东边的一处山岗上,因此,我们所看到的也只有遗址东面模糊的场景。
从老照片上观察当年的两栋房屋,似成中式传统建筑风格,靠前的是主楼,靠后的是配楼,根据宣教士所留下来的史料记载,休养所还规划有花园,在主楼前方的那一大片空闲位置,因为只有这里是最好的观景休息平台,面对瓯江,一览无余。但前方因为是悬崖陡壁,所以出入口应该不在南边,从老照片上也能看到一堵围墙圈成了半圆形,而休养所的出入口隐隐约约是朝向后面,从这里翻越山脊可以通往山下的岐头村,史料记录有村民来休养所聚会,当年宣教士有时也下山施粥或救济穷人也能说明这一点[4]。另外休养所后方的一些空地和山梯田,还能够种些瓜果蔬菜,保证日常的食物供应,节省山下或市区采购运输的困难。再有就是拍摄“番人馆”照片的宣教士因是站在东边的山岗上,也说明当时休养所后方的山上开辟有一些小道。
图:“番人馆”遗址主楼靠北东面的墙基痕迹
筆者和谢弟兄在遗址上搜索时,不但看到了一段完整的墙基,也挖到了不少青砖和石块,由此说明,番人馆是由砖石结构组成,部分砖头呈现灰红色,这是因为当年烧造的温度不够,所以出来的成品灰红相间,单簿粗糙,这类青砖和当年普通民间盖房的砖没有什么两样,厚约两公分,宽六七公分,长约三十公分,不过很多砖上都粘了一层白石灰,这和老照片中所呈现的房屋颜色相符合,可以说休养所呈现的是白墙灰瓦,符合中式传统建筑,但在内部结构布局上可能融合了西式风格。在老照片中所呈现的主楼,远看却是黑白相间,这应该是砖石加上木头的结构,和温州市区俗称“白屋”的“番人馆”有些相似,这处“番人馆”看似有半圈木(或砖木)结构的游廊。现存的墙基遗址,都是用石块垒成,主要也是为了防止台风,符合海边居民房屋的建筑性质,墙基到一定高度,上方就是青砖结构了,但是遗址上的青砖残件留下很少,应该是1929年那次台风,休养所被刮倒后,宣教士把部分的家具和物件运到山下拍卖,再后来岐头村要建立聚会点,教友们就从休养所倒塌的旧址上,搬运了那些青砖和木头,重建了山下的当地教堂[5]。
图:“番人馆”主楼北首墙基近景
图:笔者和谢弟兄考查遗址上的残砖碎瓦
查找历史可以知道,岐头山“番人馆”从建造到倒塌,总共经历了35年,恰好今年是它建造130周年。然而,这35年当中,“番人馆”也经历了繁荣到衰落,起初的休养所吸引了大量的宣教士,到这里调理度假、修养身心,包括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的女儿戴存爱以及外孙女,也曾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[6],其他一些人都陆续到过这里,例如:朱德盛(朱伯朗、蓟先生)、衡秉鑑(鑑通鉴,也译:衡平均)、查小姐(梅启文夫人)、鲍金花……等,现有的史料里都有零星记载。根据笔者深入的了解调查,刚建的休养所确实引来了不少的宣教士,特别是前十年间,因它最初是温州地区唯一的一座宣教士休养所,所以,后来其它差派的宣教士有时夏天也到这里避暑休养。况且那时候正是福音传入温州不久,传教的事工压力都比较大,身体营养也比较缺乏,但晚清宣教士的传教热情却没有减弱,再加上休养所处的位置,远离闹市,气候宜人,都成为很多宣教士闹中取静的首选。
内地会会刊《亿万华民》上所刊登的老照片,应该是疗养所建造后前期所拍摄,据当地历史学者考证,拍摄的“番人馆”照片曾在资料上刊登过两次,最早一次是在1900年,另一次是1903年,两次刊登的是同一张照片,因此,推测最早拍摄“番人馆”的照片应该是在1900年之前,或那年的春夏之际。再看两座房屋,大小结构不一,主楼是宣教士休息、接待、聚会的场所,砖木结构,整体看上去前黑后白;而配楼就是餐厅、厨房、储藏室及仆人居住的地方。曹明道在其著作里曾有详细的描述:“休养所是按中国民居形式建造的,三个房间是长的,两个房间是深的,两边各有一间卧室,中间是一个很大的起居室,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储藏室,需要的时候很方便就可变成一个房间,房屋的三边都有大过道,每条过道里最里头都是浴室,后面是厨房和佣人的房间,前面是一个小花园,花园用围墙围着。[7]”这和笔者所考查和推测的基本一致,根据描述,整个“番人馆”主楼现成的房间不超过十间,一旦遇到恶劣的局势环境,可能还需要临时增铺拥挤。但在那个年代,却为宣教士避乱、避暑、疗养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
图:烟台海边的外国建筑
图:瓯江口岐头山的休养所
奇怪的是,照片上两座房屋顶上还竖有的尖状物,是烟囱,或是避雷针,或是旗帜,还是十字架,从照片上观察,现已无法判断,笔者推测旗帜的可能性比较大。但房屋一大一小的结构却很明显,从照片上看,配楼东面墙面还开了三个窗户,而主楼的东墙面看似没有窗,判断应该是三面开放,呈现黑色的部分判断应该是环绕的游廊,而且是砖木结构,应和市区的“白屋”有些相似;主楼前方的空间也非常大,估计花园就在这个位置,因为前方面对的就是瓯江,也是休养所观赏海景最佳的位置。花园最前面正中,贴近陡崖处的围墙内,似有一块凸起的东西,不知是花园中的椅子,还是其它摆设物?又像似石刻碑之类?若是一块石刻碑,如今应该被埋在地下的某处位置,因资料没有记载,也无从考证。在当年,高高的围墙环绕着两座灰白色的房子,可以说这里是瓯江口最耀眼的房屋别筑。
笔者和谢弟兄在番人馆遗址上查找了老半天,欲尝试着掘地挖土,也始终没找到更多有价值的瓷碗、老物件或其它东西,除了几块残砖,一段比较清晰的墙基和屋后巷道痕迹,剩下的只有荒草和泥土。笔者站在原地思考,这座远离闹市,建在风景宜人的瓯江口险要位置的休养所,到最后为何会弃之荒废?是自然灾害因素?是物资缺乏?是无人打理?还是离市区太远不便?撤回的途中,笔者一直陷入深深的思考……